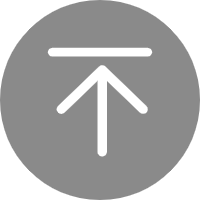那些意大利经典影片,你看过几部?
有人说,“唯有在意大利电影中,意大利才是最真实的,且是超越现实之上的情感真实。”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 意大利电影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意大利人的困窘、焦虑、兴奋、自嘲或戏谑,用灵动的方式表现深厚的人文关怀。
新现实主义:它就是生活本身
意大利电影的艺术气质与它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濒临第勒尼安海、亚得里亚海、利古里亚海与伊奥尼亚海,凛冽、浓艳、温和、平静,不同的景观意象赋予它不同的风貌与精神气质。而意大利电影的辉煌,则要从台伯河(又称特韦雷河)孕育的罗马说起。
1905年,意大利电影人于罗马创立电影制片厂,之后都灵、米兰、那不勒斯、威尼斯等地也建立了小电影公司,拍摄由历史题材和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二战时期,墨索里尼将电影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任命其子管理电影业;一些导演拒拍庸俗商业片和鼓吹法西斯思想的宣传片,拍摄了一些只注重作品形式探索而被后世称为“书法派”的电影,即“走形式流,要精致”。
1945年,墨索里尼垮台,曾经孕育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正在迎接又一次重生。受战争重创,二战后的意大利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失业率极高,人民生活贫困。电影界更是面临资金匮乏的窘境,电影人不得不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实景拍摄;同时,他们不满现实,渴望用电影来反映意大利的现实状况及战争造成的民族悲剧,因而几乎都有意无意地拍摄了反映战后意大利社会问题的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就在那一年8月横空出世,标志着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学派的诞生,亦成为意大利电影史上一座无法超越的丰碑。

《罗马,不设防城市》被公认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真实反映了意大利人民在德国占领时期的生活和斗争。在这部“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宣言书”中,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把摄像机搬到因战争瘢痕累累的大街上,罗马的废墟成为电影的独特背景。影片第一次集中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对现实生活做历史的、具体的处理,对当时生活条件进行尖锐的批评、对普通人民的苦难表示真诚的同情;采用自然实景,人物角色经常由非职业演员扮演,集中描绘工人、农民、小市民和城市知识分子的状态;主要取材于新闻报道,绝不采用虚构臆造的故事。
新现实主义影片中那些倒塌的楼房、丑陋的贫民茅棚、世俗的人物影像,聚焦了战后的社会问题,揭露了底层人民残酷的生活现状。其“批判性的人道主义电影”潮流,不仅开创了独特而鲜明的电影风格,更将其影响力传播至全球。
1946年,罗西里尼拍摄了后来“迷住”妻子、好莱坞巨星英格丽·褒曼的《游击队》,展现了战争年代意大利人生活的真实图景;翌年,他又拍摄了以12岁德国男孩埃德蒙的战后遭遇为主线的《德意志零年》,最终瘦小的男孩从残破不堪的高楼上无望地跳了下去。这一跳,完成了影片最为震撼的一幕,也完成了罗西里尼最为深刻的一次批判。

罗西里尼和妻子英格丽·褒曼的生活照

《德意志零年》剧照。毒杀父亲的埃德蒙独自一人游走在街头,最后一跃而下告别短暂一生,他熬过了战争,却没熬过战后的重建,借此痛斥法西斯主义。
1952年,朱塞佩·德·桑蒂斯(Giuseppe De Santis)根据一桩惨案拍成《罗马11时》:战后,一家公司招聘一名打字员,几百名妇女一大早就争先恐后来应聘,你推我挤,结果楼梯倒塌。影片的结局精妙且引人深思:警察调查后,最终不了了之,而大楼外仍有一个姑娘在等待,希望得到这个唯一的职位。

《罗马11时》剧照,上百名女子为应聘一个打字员职位挤在楼梯上,造成楼梯倒塌。影片真实反映了战后意大利经济复苏时期的社会现状,揭露了当时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是具有社会批判力度的杰作。
同样取景于罗马、表现失业困苦的名作,不能不提切萨雷·柴伐蒂尼编剧、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执导、1948年上映的《偷自行车的人》:失业多时的里奇费尽千辛万苦获得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他赎回已当掉的自行车方便沿街工作,却不想上班第一天车就被偷了。里奇和儿子寻遍罗马大街小巷未果,最终决定“以牙还牙”,却被当场捉住受辱。摄影机跟着里奇父子在罗马的大街小巷中穿梭:人群拥挤的职业介绍所、破烂简陋的工人居住区、物品堆积如山的当铺、熙熙攘攘的自行车市场、教堂、妓院、贼窝⋯⋯电影犹如战后意大利现实的全景画。

德·西卡为演员索菲亚·罗兰讲戏

德·西卡作品《偷自行车的人》
“宁肯要现实而不是浪漫故事,要世俗而不是闪闪发光,要普通人而不是偶像”,通过镜头实现对现实各个方面的深入观察和细致分析——新现实主义电影,在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看来,就是“真实美学”。所以,我们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中看到纳粹德国士兵的暴行,在《偷自行车的人》中看到生活的窘迫,在《两分钱的希望》中看到迫于生计去拉马车的退休士兵,在《游击队》中看到在枪林弹雨的佛罗伦萨街头奔向爱人的少女⋯⋯罗西里尼曾用一句话定义新现实主义电影:“它就是生活本身。”

《游击队》剧照。罗西里尼在摄制该片时,拒绝用摄影棚、服装、化妆和专业演员,力求展现战争年代意大利人民生活的真实情景。
艺术电影:美学风格的转向
与《德意志零年》类似,德·西卡1946年拍摄的《擦鞋童》也以战后欧洲底层儿童的生活为内容。但出生于第勒尼安海边那不勒斯的德·西卡,一如巴赞所言是“电影诗人,在用那不勒斯人特有的和煦性格拍电影”。而那不勒斯这座北方工业文明与南方农业文明互相碰撞的城市,也作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奇遇》主人公的旅途中转站,带给影片强烈的象征意义:一男一女寻找失踪的朋友安娜,影片没有表现安娜失踪的来龙去脉,而是致力于表现两人之间难以沟通的情感。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寻找,一次没有结局的失踪。所谓找寻安娜的过程,其实暗指这些人都濒于失踪的边缘,生活如此不真实,关系如此脆弱,他们“停泊在各处,但从来都与故事没有丝毫关联”。其实,早在1955年,安东尼奥尼执导的《女朋友》就将重点放在人物特别是中上层社会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表现了“人在思想感情上的不可交流性”和“感情关系的脆弱”。

安东尼奥尼(1912年9月29日〜2007年7月30日)

安东尼奥尼执导的《女朋友》侧重刻画上流社会人物的内心世界
直观来看,《奇遇》和《德意志零年》《擦鞋童》完全不是一个“路数”的电影。上世纪50年代以后,意大利电影的美学风格由现实主义开始转向神秘幻想、象征主义以及文学题材,进入现代主义电影发展阶段。诸多导演的作品都力图进一步打破以往电影的叙事规律、淡化情节与故事,而去表现个人的意念、回忆和想象,并把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不可知论掺入电影中。这种转向的根源是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危机”——意大利经济得以复苏,中产阶级的人数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观众对新现实主义电影“直白的描述”深感不足,他们希望更加艺术化、多层次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向往回归古典式的浪漫。一如安东尼奥尼的名作《放大》:摄影师在公园抓拍年轻情侣,出人意料的是照片中的女子不惜一切代价要回底片,这让摄影师非常疑惑,他把照片放大后,看到了一具尸体和一个拿枪的人。一桩谋杀案的雏形在他脑中展开,他前往公园寻找到了尸体,然而次日他再来到公园时尸体已消失无踪,只有一群人正进行着一场虚拟的网球赛,打着并不存在的网球——导演用这个迷离的故事,叩问真相与幻想之间的界限。
“新现实主义,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现实,还应包括精神现实、超自然的现实和任何可能具有的事物。”青年时代曾与罗西里尼合作创作《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和《游击队》的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像罗西里尼一样,将夫人作为电影的真正灵魂——朱列塔·马西纳主演了他的多部电影,她的脸庞纯真、感伤、滑稽、略带忧郁而又不失狡黠,这种特殊的形象气质就如他喜欢的马戏,赋予他日后的电影丰富的想象力、对色彩的敏感和极端个人主义风格。

费里尼妻子朱列塔·马西纳在《卖艺春秋》中的剧照
从1950年的《卖艺春秋》开始,费里尼的作品就与新现实主义正统的批判意识和平民主义形成鲜明对照。1954年的《大路》利用一次旅程去表现两个完全属于不同世界的人的心路历程,在费里尼看来,《大路》“是将自我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是重视自我的一次冒险”。而对电影史而言,《大路》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背离”新现实主义传统的电影,它不再拘泥于对现实的“复原”,而开始转向内心化,从而引发战后意大利文艺界第一次美学大论战,唯物电影论被扬弃,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电影”得以诞生。

《大路》是费里尼从新现实主义开始蜕变为新现代主义派的转型作,影片中马西纳对傻女人的演绎极其出彩。
在巴赞看来,《大路》《骗子》《卡比利亚之夜》组成的“孤独三部曲”中,《卡比利亚之夜》“标志了新现实主义旅途的终点”:在这部凄清的作品中,下层妓女卡比利亚受尽生活中的侮辱、嘲弄与欺骗,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喘息求生。影片结尾,她茫然地走在街道上,看着一群边走边唱的年轻人,慢慢从空虚的心境回到现实,重新露出微笑。这个奇妙而模糊的暗示,意味深长。
暗示不模糊而意味同样深长的是费里尼1959年拍摄的《甜蜜的生活》。它讲述花边新闻记者混迹于明星、富豪们的生活,目击上流社会寄生虫的虚浮、矫饰和堕落。电影一开场,费里尼就将宗教、古典文化与颓废的气息表达出来,从那些性感的女人、充满象征意味的小丑、奢侈淫逸的场面、光怪陆离的情景和难以遏制的欲望开始,他不但完全脱离了写实主义,更加强了幻想甚至超现实的处理手法。讲究的镜头、华丽的布景、刻意的人物造型决定了《甜蜜的生活》在意大利影坛的地位:它宣告了费里尼从早期的新现实主义走入象征主义,也把一面镜子送给虔诚相信“经济奇迹”与“改革进步”的意大利。尽管它引起了轩然大波——梵蒂冈教廷反对这部“图谋不轨”的电影,社会右派怒火中烧,左派也批评导演态度不明地展示颓废、脱离了底层人民,但它在国际影坛斩获多个奖项,更被电影史学家们视为“可与但丁《神曲》并称的艺术巨作”。

费里尼的作品《甜蜜的生活》讲述了花边新闻记者混迹于明星、富豪队伍,在腐朽、空虚的生活中挣扎并最终继续堕落的故事。
但费里尼还没有达到顶峰。直到1963年他拍摄了自传体电影《八部半》,叙述了“一个处于混乱中的灵魂”:一个缺乏灵感的导演来到温泉疗养院疗养,监制、编剧、演员无休止地催促他开戏,妻子与情人又争风吃醋,导演快被逼疯。在这个普通人的厄运与痛苦中,费里尼加入了童年的回忆、构思中的电影桥段与天马行空的幻想。故事情节简单,却成功反映了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堪称“用摄影机探究人物内心的一次伟大尝试”。费里尼桀骜不驯的艺术禀赋和强烈独特的个人风格,使他与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并称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深刻引导了战后意大利电影的艺术发展进程。

费里尼在《八部半》片场给男主角马塞洛·马斯楚安尼讲戏
文学与地域:关注相互冲突的文化
如果新现实主义电影倡导的是“另一种拍电影的视角”,那么1932年开始举办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宣扬更多的是“另一种看电影的眼光”,这在意大利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和威尼斯温柔浪漫的人文环境下显得顺理成章。
亚得里亚海边的威尼斯,被记录在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的《魂断威尼斯》中:黄昏,笼罩着粉色和金色薄雾的亚得里亚海上驶过一艘白色轮船,圣马可大教堂金光闪闪地在观者眼前突现,带着肃穆和炫目的美丽。《魂断威尼斯》讲述的是比电影节更早光临丽都岛的德国作曲家艾森巴赫在饭店看到美少年达斯奥后,便狂热地追寻这位少年,哪怕霍乱上身,最后倒毙在金色沙滩上。沙滩上,达斯奥和同样青春的泳装男伴在追逐嬉戏。艾森巴赫生前最后看到的是达斯奥纤细的手指指向无尽的远方。

《魂断威尼斯》中的美少年剧照
貌似是忘年同性柏拉图之恋的故事,实则展现的是对永恒之美的深刻追求——维斯康蒂的作品总是充满浓厚的文学、戏剧韵味以及深刻的哲学思索,这源于他贵族出身熏陶出的尊重古典的观念和浓厚的戏剧气息。像维斯康蒂一样热衷于将文学作品搬上银幕的还有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他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统统加以影像展现。
维斯康蒂也有反对贵族之血的革新思想,早在创作初期他就反对独裁,以平等的原则执导影片。1948年上映的《大地在波动》取景于西西里岛的渔村,拍摄时不用职业演员,现场临时改剧本、写对白,全片使用西西里方言,意大利人观影也需配合字幕才能看懂——当时意大利约有75%的人使用方言,大部分是底层民众。而在1963年,西西里岛又成为维斯康蒂的《豹》中留恋古老传统秩序的故事的“原点”。

维斯康蒂的影片《豹》以19世纪60年代的西西里岛为背景,讲述了面对动乱的社会变革,旧体制贵族的没落,并最终被新兴阶级所取代的宿命。
位于伊奥尼亚海中的西西里岛是意大利电影的宠儿。那里传统的生活方式、激烈的黑帮斗争、虔诚的宗教信仰、美丽的自然风光、古代的文明遗迹,在电影中亦被赋予了别样的韵味:《豹》的华丽、《天堂电影院》的温馨、《吾父吾主》的蛮荒、《邮差》的清丽、《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凄艳⋯⋯这里也是罗西里尼与新婚妻子褒曼合作的《火山边缘之恋》的拍摄地,代表了他的转型——关注相互冲突的文化。
提到西西里,影迷的第一反应非《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莫属。西西里小镇上的少年雷纳多骑着脚踏车,“跟踪、偷窥”风情女人玛莲娜。直到玛莲娜的丈夫死讯传来,她的父亲也死于战火轰炸,无依无靠的她为了生存不得不委身于一个个好色的男人,包括德国人。在盟军占领西西里后,她被嫉妒得红了眼的女人们剃光头发、脱光衣服后游街示众。电影结局更显匠心独具:讹传已经战死的丈夫最终带着她回到西西里,镇上的人接受了她,但丝毫没有忏悔,因为此时的玛莲娜已不再拥有惊人的美丽,只是个平庸的家庭妇女,只有在雷纳多心里留下了关于美丽的传说。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Giuseppe Tornatore)镜头中的西西里温馨而残酷,幻想兼具写实。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莫尼卡·贝鲁奇饰演的玛莲娜风情万种地穿行锡拉库萨大教堂广场是影片最经典的桥段之一。
相比“文艺”,西西里带给意大利电影的另一显著特点,非黑手党莫属。上世纪60年代,《黑手党人》《龙头之死》《黑手党》等电影,都以现实主义而非类型片的态度与手法来展现故事,倾向于冷峻地揭露社会政治的现实。而在70年代,意大利黑手党文化为已经僵化的黑帮片理想男性主人公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们更为男性化,将形式主义的暴力美学直接导入男性形象,主人公变得更加凶残和无所顾忌;同时,他们又更“女性化”——黑手党独特的家族观念与血缘情感,彻底改造了以往黑帮片对家庭和家庭关系的无视,一个单枪匹马如野兽般求生于都市丛林的男性突然被拉回到一个更加“现实主义”的家庭环境中,这个家庭环境构成了黑帮人士的事业主线。在外,黑帮可以冷血狠绝、叱咤风云,但回归家庭,他们就是拥有儿女情长的大家长。

《教父》是意大利裔美国导演科波拉执导的经典黑帮片,描述了柯里昂黑手党家族的兴衰,该片为美国电影史上的犯罪片开拓了宽广的前景。
意大利黑手党独特的组织结构和人物形象,成为“新好莱坞”时代之后西方黑帮类型片的文化支柱,甚至让一批意大利后裔电影人成为现代黑帮片的代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布莱恩·德·帕尔马、阿尔·帕西诺、罗伯特·德·尼罗、詹姆斯·凯恩⋯⋯
多元变革:始终表现它的时代
热衷于拍摄西西里的托纳多雷有着意大利南方人天真热情的性格,他的诸多作品都充满对现实问题的关注,1989年他因《天堂电影院》一举成名,这部电影也被视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传统复兴的起点。意大利资深电影评论家恩里克·马格莱利这样评价:“他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不赶潮流、不追逐时尚拍电影的人。他始终坚持自己讲故事的方式。”

《天堂电影院》中,对电影和放映机的共同爱好,让放映师阿尔弗雷多和小男孩多多成了忘年交。
“坚持自己讲故事”的还有罗伯托·贝尼尼(Roberto Benigni),其代表作是《美丽人生》:平民圭多爱上贵族小姐多拉,这段爱情故事是典型的意大利喜剧,而影片后半段则以黑色幽默语调讲述集中营故事。初到集中营时,为了防止战争在儿子心中刻下烙印,圭多站在德国人旁边冒充翻译,假模假式学纳粹军官,却把他宣布的集中营规则变成游戏规则,这也是电影的核心情节——以戏谑态度对待人生荒谬,以乐观精神对待人性丑恶。

《美丽人生》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描述了圭多一家在纳粹集中营中的悲欢离合,展示了圭多对美丽人生的憧憬和在残酷环境中特有的乐观。这部电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二战题材的影片,它是一幕黑色喜剧,以一种超越常规的新鲜视角呈现二战历史的一个侧面。导演兼主演罗伯托·贝尼尼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为在二战中受伤的人们注射了一针止痛剂。

《美丽人生》剧照。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圭多一直“欺骗”着儿子乔舒亚,告诉他说这是在玩一场游戏,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最终能获得一辆真正的坦克回家。父亲对孩子无私的爱触动人心。
“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将我自己、我的喜剧主人公置于一个极端的环境之中,这种最为极端的环境就是集中营,它几乎是那个残酷时代的象征,消极面的象征。我用一种喜剧的方式描述一个有血有泪的故事,因为我并不想让观众在我的影片中寻找现实主义。我认为,真正的喜剧都是由悲剧悲情的线索延伸出来的,所有喜剧让人发笑的元素中最核心的部分都是悲剧。”贝尼尼说。这就是意大利人的态度:性格中的深沉和乐观、戏谑与无奈,交织出骄傲和天真。
在经历了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辉煌,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名导的承继与发扬后,尽管喜剧电影和政治电影也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和地位,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意大利电影还是衰落了。世界范围经济危机带来的艺术困境、日益增加的生活压力,让人们更倾向于去看娱乐性电影而逃避现实。意大利没能及时建立一套响应全球竞争的经营体系,以致将国内60%的市场拱手让给好莱坞。在这一时期,维斯康蒂、罗西里尼、德·西卡、帕索里尼等人相继辞世,更使电影业界雪上加霜。
有评论认为,“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是,电影在意大利主要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表达而不是商业产品。” 因此艺术电影的成就,毫无疑问构成了意大利电影兴衰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在暌违世界顶级电影节头筹近十年后,2001年,意大利导演南尼·莫莱蒂(Nanni Moretti)的电影《儿子的房间》一举拿下当年戛纳金棕榈大奖,举国为之欢腾。21世纪以来,意大利电影正在复苏,《海上火焰》《绝美之城》《饥饿的心》《罗马环城高速》《凯撒必须死》《我的母亲》《为父寻仇》《教皇诞生》⋯⋯屡获电影界重要大奖,颇为业界瞩目。

《儿子的房间》中南尼·莫莱蒂一改以往的诙谐风格,以温情的画面、朴实的对白和简单的情节讲述了一个沉重的故事,平实自然,却感人至深。
意大利电影始终在表现它的时代,就如托纳多雷那部颇具史诗片质感的《巴阿里亚》,故事从20世纪30年代跨越至60年代,讲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十年间一家三代人经历的生活变迁。

《巴阿里亚》的史片格局和宏大叙事,充分彰显了导演托纳多雷力图呈现“意大利社会的万花筒”的野心。
普通人的命运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中如浮萍一般——这是意大利电影;而因脑血栓被迫远离摄影棚多年的安东尼奥尼在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协助下拍摄的封镜之作《云上的日子》,这同样是意大利电影:一个导演漫无目的地在4个城市游荡,以回忆、冥想的方式连缀了4个独立的情爱故事,让观者深刻体验到现代世界的扑朔迷离和隐匿在技术文明背后由感情真空造成的焦虑。而影片伊始,导演的独白,或许可以成为意大利电影的一种注脚——“我陷入深思与黑暗,在黑暗之中,线索得以被燃亮,在沉默中外界的声音逐渐渗入。我相信万物里有一种动力,驱使我前行,它是生命、过去和未来的源泉。”